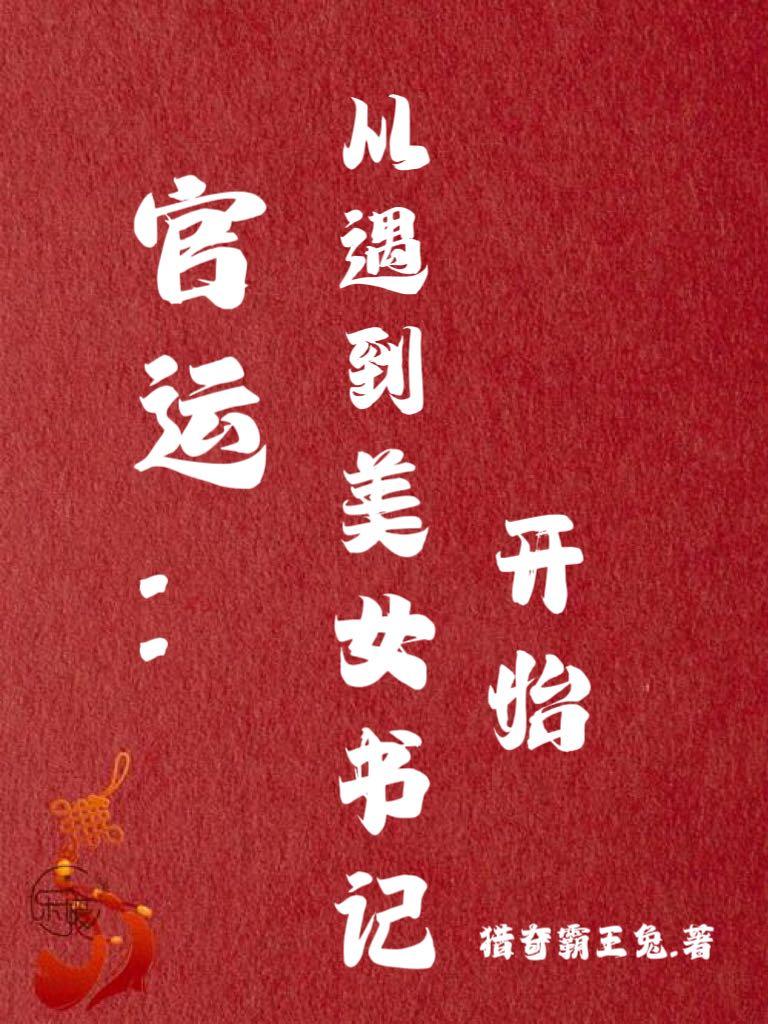林斌蹲在時歡面前——他是通緝犯,為了不被人認出來,特意做了喬裝。
下巴留了胡渣,頭發也接長,劉海蓋住額頭,額頭不知道用的什麼道具做了非常逼真的大片傷疤,哪怕是近距離也很難看出來是假的,他對外宣稱,小時候遇到大火被燒得毀容了。
“你的胃口也太大了,CFO?溫尚傑肯定不會讓你當,就算有溫董力挺你也很懸。”
時歡想過了:“溫董手裡原本持有溫鹿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,這些年被溫尚傑搶了三十,他也還有二十一,隻要他把這股份分一些給我,我就有進董事會的資格。”
“溫董應該沒意見,給親孫女的見面禮,合情合理。”林斌道,“但有股份也不夠,你頂多就是占一個董事的身份,想要公司實權,還得再想想别的辦法。”
确實,還不太夠,還得有别的辦法。
但她必須當這個CFO,否則在溫鹿和溫家都站不穩腳。
院子裡起了一陣風,時歡手上的賬本陳年老舊,已經開線,被風一吹,紙張飛了起來。
她連忙去撿,一根黑色的手杖及時按住紙張,沒有讓它飛進污水。
時歡擡起頭,對上周自珩溫和的眼眸。
她一笑:“周自珩,你怎麼來了?”
林斌起身回屋,給他們騰地兒。
周自珩收了手杖,撿起紙張,到她面前遞給她。
時歡說:“謝謝。”然後伸手去接,捏住了紙張,卻抽不回來,周自珩沒有放開手。
時歡疑惑地與他對視,周自珩看進她的眼睛,輕聲問:“難吧?”
時歡坦然:“難,但是我自己選的路,無論如何我都會走下去。”
周自珩:“我可以幫你。”
時歡的瞳眸迎着光,是琥珀色的:“怎麼幫我?”
周自珩站直了身體,也将手遞給她,要拉她起來——這個動作,一語雙關。
“我們的婚約,可以幫你進入溫鹿的權利核心。”
是的。
溫家大小姐和周家大少爺,是有婚約的。
而周氏,現在是溫鹿要緊緊抓着,絕對不能放手的救命稻草。
時歡眸子閃了閃,幾秒之後,她将手放在了周自珩的手掌上。
周自珩稍微一用力,将她拉了起來,也将她從困境中拉出來。
……
于是,這個事情,也在周自珩公開向溫尚傑提及後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,傳遍圈内。
林景舟收到消息已經是晚上十點多,坐不住,開車直奔江公館。
江公館的門衛認得他那輛車,遠遠就給他開門,他一個漂移,将車停在2号樓,接着刹車、挂擋、拔鑰匙、推開車門,動作一氣呵成。
他幾步跑進去:“二哥,二哥!”
夏特助出現在二樓,忙對他做了一個噓聲的動作,林景舟跑上二樓,江何深從嬰兒房出來,順手帶上門,面無表情地看着他。
夏特助低聲:“少爺好不容易才把小小姐哄睡,您别又吵醒她。”
林景舟從善如流地壓低了聲音,一個字一個字地說:“小!嫂!子!要!跟!周!自!珩!訂!婚!了!”
夏特助:“?”
夏特助:“!”
江何深身後是走廊的壁燈,逆着光,他臉色一片晦暗。
林景舟真誠地點頭:“周家已經在印請柬了。”
夏特助驚訝到說不出話:“……怎麼會這麼突然呢?”
林景舟聳了聳肩:“不算很突然,溫家和周家本來就有聯姻的關系,隻是之前一直是周自珩跟溫隻顔,小嫂子成為溫家大小姐後,這樁婚約就順理成章地轉給了她。都已經定好了婚期,就在下個月三号。”
夏特助又被刷新了認知:“這種事情也能轉?”
“怎麼不能?”林景舟笑,“豪門聯姻,本來就不講究真感情,利益才是第一位。”
順便舉了個例子,“京城兩大豪門,謝家和戚家的聯姻,謝二小姐已經當了戚大少爺十幾年的未婚妻,誰知一夜之間,謝家走失多年的大小姐找回來,現在圈裡也在傳,戚謝的婚約要換成大小姐。”
夏特助:“……”
确實是他見識短淺,閱曆不夠深。
可是:“溫隻顔也沒有意見嗎?溫尚傑也沒說什麼嗎?”
林景舟靠在欄杆上:“溫、周兩家之所以會聯姻,是因為周董和溫董以前是戰友,兩人在戰場上有過命的交情,現在溫董做主把婚約給小嫂子,隻要周家沒意見,溫家人就沒有資格有意見。”
夏特助難以評價,隻能看向江何深。
江何深表情寡淡,眸色比窗外的月還要清冷。
林景舟撓撓眼頭小痣:“不過我猜,小嫂子是想用跟周自珩的婚約,在溫家站穩腳跟,這一步走得很妙,确實有用。畢竟溫家現在肯定不敢得罪周家,他們這次訂婚,應該是勢在必行。”
江何深擡起了眼:“說完了麼?”
林景舟站直了:“不是,二哥,都這樣了,你還不做點什麼?”
“我需要做什麼?”江何深冷冷,“要我把離婚證給你看麼?”
意思就是,他們已經沒有任何關系,她想跟誰訂婚,想嫁給誰,都随便。
林景舟豎起大拇指:“行的,你沉得住氣就行。”
又不是他老婆跟人跑了,既然他都不操心,他就更不操心了。
林景舟不說了,打了個哈欠:“困了。小夏,讓人收拾間客房給我,我今晚睡在這兒。”
不用收拾,2号樓的房間多的是,都是幹淨的,夏特助馬上為林景舟帶路,去了三樓的客房。
随着他們離開,二樓走廊上隻剩下江何深。
十點後的2号樓,永遠是這麼安靜,燈光将江何深落在地上的影子,拉出了永恒的緘默。
江何深進了主卧,依次摘下手表、扳指、戒指,放在梳妝台上——放在時歡留下的那個盒子旁邊。
這個盒子,從嬰兒房移到主卧,但他到現在都沒有打開。
他漠漠地看着,拿了睡衣進了浴室。
浴室水聲淅淅瀝瀝,片刻後他洗完出來,用幹毛巾擦着濕發,走到落地窗邊,将窗簾拉上,轉身又看到那個盒子。
幾秒後,江何深終于丢下毛巾,走了過去。
盒子并沒有貼上膠帶,很容易就能打開。